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媒介(Mediation)研讀班No.1】沒有我們的世界
撰稿/逢甲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鄭如玉
攝影/國立政治大學英文系碩士班鄭茗方
主題:沒有我們的世界
導讀書目:Eugene Thacker, In the Dust of This Planet
主講人:黃涵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主持人:李育霖(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
時間: 2019年1月26日(週六)
地點:台灣師範大學誠大樓八樓英語系會議室
主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

(黃涵榆老師主講「沒有我們的世界」)
在本場研讀班開始之前,首先由邱彥彬教授簡短說明「媒介」系列研讀班的宗旨。他指出研讀班將處理三大重點:怪物、AI與新媒介。媒介指的是打開一個 「通道」(passage):有了通道,訊息(message)才能流動而產生溝通(communication)。按麥克魯漢的觀點,訊息本身可能是模糊不清、曖昧不明的。如此一來,媒介本身就會成為重點。例如在新物質主義的發展中,物自身的物質性與科技媒介的傳遞過程變得非常重要,同時媒介如果不存在,人直接面對意義的空無,又會連結到怪物或惡魔等想像。
接下來,在主持人李育霖教授簡短開場之後就由黃涵榆教授開始導讀。黃教授先提到本場次的主題偏向暗黑、恐怖等議題。他個人對尤金・薩克(Eugene Thacker)的書有興趣有兩個原因:一是多年前某「歐巴桑」告訴他「死無恐怖,通驚死未去的彼種情形」,使他對事物死後,或者人類滅亡之後,世界會以何種形式延續下去的問題產生興趣;另一個原因則是薩克的書廣泛涉及哲學傳統、政治神學、古典與通俗文學、文化等,取材非常豐富,他特別喜歡講亞里斯多德、但丁、拉夫克拉特小說、伊藤潤二漫畫和黑金屬等題材。
哲學的恐怖
薩克這本書In the Dust of This Planet 是「哲學的恐怖」(The Horror of Philosophy)三部曲中的第一本。「哲學的恐怖」是一種悖論(antinomy),表示哲學思考依著理性走到理性的界限,面對無法思考的非人世界的境況。從書的引言看,薩克似乎想要將整個西方理性主義的、形上學哲學傳統裡那些被壓抑的、被排除的思想碎片全部挖出來。包括惡魔學(demonology)或者諾斯替神秘主義之類的,所謂的哲學周邊領域都變成重要資源。這種恐怖跟通俗故事的恐怖類型不完全相同,雖然薩克對某些恐怖類型好像特別有興趣,尤其是恐怖作家拉夫克拉特(H. P. Lovecraft)的作品似乎與其論述一拍即合,但是黃教授認為這部分可以留待後續處理。按薩克自己的說法,他要談的主要還是把哲學當成一種恐怖。當理性走到理性的界限,進入到不可思考的世界,就會形成思考的悖論:只有憑藉思考,我們才能面對無法思考的非人世界。有點像精神分析學中所談的莫比烏斯環(Möbius strip)。
詮釋世界的方式
薩克整理出三種詮釋世界的可能方式:神話式的、神學式的與存在主義式的。神話式詮釋指的是:我們面對一個由個人情緒與恐懼所投射出來的神話世界。神學式詮釋以基督教觀點為代表,指的是世界的變化背後有一套很龐大的道德系統,充滿是非、善惡、對錯等對立關係。存在主義式詮釋則比較關心人在世界所佔的位置,或者說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事對人的生命有何意義。薩克認為,以上三種詮釋方式都是以人為中心。所以我們要檢驗的就是薩克是不是真的跨出以人為中心的觀點,走進或者至少讓我們看到所謂不可思考的、無人的世界。
薩克將世界分成三個層次:「世界自身」(the world in itself)、「我們的世界」(the world for us)與「沒有我們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第一層次「世界自身」對應到地球,比較像是科學在探討的世界,我們較強調它客觀的存在。我們沒有辦法完完全全捕捉到這個客觀世界,但我們總是能夠把它轉換成為第二個層次「我們的世界」,對應到一般意義下的「世界」。這裡我們重視的是客觀存在對人的存在有甚麼樣的意義。當然,這個層次與「世界自身」也許並非百分之百相容,特別像發生大規模的天災時,我們可能會理解到自然界客觀的某些部分並不是我們能夠掌握與理解。
今天要講的重點就是沒有我們的世界,薩克把它對應到星球(planet)。他在講述這個星球或者沒有我們的世界的時候,用了一系列的關鍵字,包括像fuzzy、spectral、liminal 和nonhuman(5-6)。我們也許可以從這一系列關鍵字去揣摩一下他所講的這個沒有我們的世界的特質到底是什麼。比較簡單一點來講的話,就是它既不是所謂主體層次的「我們的世界」,也不是客觀層次的「世界自身」。以前黃教授上精神分析時講到詭奇(uncanny),同學總會問說uncanny是存在於外在世界,還是的主觀情感,黃教授只能暫時回答說都不是。所以他的建議是我們解釋沒有我們的世界,也可以從這個角度思考,即是它存在的樣態基本上是沒有辦法用傳統主體或是客體的角度去理解。這也顯現出這一系列的哲學思考有一個很嚴肅的挑戰哲學的目的。至於薩克之前是否有人做過這種嘗試,其實也是有的,例如他滿常引用的哲學家叔本華。
薩克與思辨實在論
薩克的思想跟思辨實在論(speculative realism)其實有非常多的關聯,他與梅雅蘇 (Quentin Meillassoux)在做的事情有點像。梅雅蘇用一個概念叫「關聯主義」(correlationism)來稱呼從康德以後的哲學發展,關聯論強調人類跟世界之間的關聯,同時也劃定了人類知識到底能走到哪裡去。當我們跨出人類的框架,用哲學的語言來講,就是進入所謂的物自身,基本上就進入一個無法形成確切知識的領域,但是人跟它還是會有一點關聯。在康德的哲學裡面就提出範疇的概念(categories),對於那些超出人類經驗範疇之外的東西,我們只能用像類似時間、空間、質與量這些很抽象的範疇來維持某一種關聯。但是梅雅蘇不認為我們只能走到這個層次,他特別強調那些沒有辦法思考的物自身的絕對性:它雖無法被思考,卻並不表示不存在。放在哲學的脈絡裡來講,所謂人類思考之外的東西可以沒有任何理由就存在,卻是具有相當程度的絕對性。我們常常會講到暗黑與看不見,但是薩克又說它黑到你沒辦法去否認它,所以不是單純看不見,就像梅雅蘇也認為,有些東西你沒辦法循著理性去證明它的存在,卻是絕對存在的。這應該就是整個引言的重點。
另外,類型恐怖裡有一種主流的論述,大致把怪物視為隱喻(metaphor)或症狀,糾結了這個社會或者人類的某些情感,不管是恐懼或者怨恨,基本上都是以人為中心的一種投射。不管你把怪物想像得多可怕,他都還是一個個人或是集體的防衛機制所投射出來的結果。黃教授提到過去自己在做恐怖研究時也曾被嘲諷,認為他用精神分析來談恐怖談到最後都有點百搭,最後怪物都代表著壓抑的回返(return of the repressed),這促使他去思考有沒有其他的路數可以依循。他認為薩克正提供了我們跳脫出那種淪為SOP的操作模式,讓我們可以不再把怪物或鬼通通當成人類情感的一種投射,一種人類壓抑的回返。
黑金屬:三種層次的黑
第一章一開始,我們進入惡魔學的領域,所謂惡魔學,簡單的定義就是有一套知識或者信仰的系統在談惡魔(demon),它會隨歷史、社會、文化與宗教的脈絡不同而與時俱進,發展出不同的惡魔系統。這一章主要談的是黑金屬。書一開始就解釋:黑金屬的「黑」其實總是脫離不了惡魔(demons)的概念。薩克將黑金屬當成思考魔的出發點,也會從這樣的角度深入討論哲學的恐怖到底指的是甚麼,如何把哲學思考推向一個不能再思考的、非人的境域。
薩克提出三種層次的黑:跟撒旦崇拜有關的黑、與異教信仰有關的黑以及從宇宙悲觀論的角度來談黑。首先,第一個層次的黑是跟撒旦崇拜有關的。在以西方基督教為主的傳統脈絡裡,撒旦的形象經歷了滿悠遠的歷史變化過程。他曾經被當成上帝或基督教教會系統的敵人,形成一種對立的關係,在政治神學上等於是挑戰了以神為中心的政體。可是這種對立關係隨著時空脈絡的演變,變得越來越複雜。所以接下來單純對立的關係可能會進一步發展為倒置(inversion)。我們讀惡魔學的歷史發展,會發現19世紀時有一股頹廢的、世紀末的暗黑文學跟文化潮流,非常著迷於魔的概念上,使魔被賦予了很多個人主義、英雄主義或者是美學的情趣在裡面。不論如何,在基督教主流信仰發展的過程中,第二層次,也就是與異教信仰有關的黑被邊緣化。這個部分跟自然與動物的力量有關,包括黑金屬或者重金屬中嘶吼的聲音,就是一種回應大自然野性的呼喊。
以上兩種黑其實都不是薩克要談的重點,他基本上會比較從宇宙的悲觀論這個角度來討論黑金屬,特別是黑金屬裡面黑的特質。頁17有個例子:漠不關心(indifference)這個字指的是人的努力被漠視,變成可有可無,或者是說這個世界可以沒有任何目的,其變化跟人的介入是脫鉤的,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從理性行動或目的的角度去理解這樣的世界。薩克談到人類滅絕後沒有人會去想像沒有人的世界如何絕望,使我們體認到宇宙悲觀論的深沉。頁18介紹了叔本華對哲學的恐怖的重要性,包括他挑戰了凡存在必有理由這種思考,或者是顛覆了傳統主體跟世界之間的關聯。在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有一個關鍵字意志(will)。一般在理解這個字的時候都是把它連結到理性的人類行動力;但是對叔本華來講,意志基本上不能理解為人採取行動的主觀原則,而是一種非人的、盲目的生命力。薩克從宇宙悲觀論的角度來討論黑金屬,除了叔本華之外也提到拉夫克拉特,以及當代日本很重要的金屬音樂大師灰野敬二(Keiji Haino)。
黃教授指出如果要挑薩克毛病的話,我們可以說他談黑金屬的方式似乎太過抽象化哲學化,因此沒有注意到黑金屬作為表演的各種不同的面向,包括視覺、圖像、顏色與聲響等。比如說顏色,我們一般講憂鬱會聯想到黑,薩克也提到暗黑與黑膽汁等,可是這其實是會變化的。在浪漫主義時期,浪漫主義詩人的畫像都被畫的很白,表現他們的憂鬱,可是憂鬱不是應該跟黑膽汁(黑)有關嗎?所以在西方文化史發展的脈絡裡面,憂鬱既是黑的又是白的,是一種弔詭又曖昧的混合體 (mixture)。
我們可以在黑金屬表演者身上看到這種弔詭的黑白混合,特別是黑金屬有一種叫屍妝(corpse paint)的化妝方式,大致上是強調黑跟白之間的強烈對照。所以如果西方啟蒙思想代表的是太陽中心論,這些人基本上就是要挑戰光跟太陽所帶來的理體中心主義。他們的妝還有一些宗教上褻瀆的意味在裡面,有時他們把自己扮成教皇,但是手上拿的不是權杖,而是像象徵惡魔的三叉戟之類的東西,有時候還會掛一個鮮血淋漓的豬頭,作為撒旦膜拜儀式的象徵。
惡魔學的發展
另外第一章有提到惡魔學發展的歷史,第一種惡魔類型的發展脈絡是從宗教上的誘惑者或者敵人開始,慢慢跟人的情感與慾望越來越糾纏不清,所以有人用「人類學化」(anthropologize)來形容。以比較積極的面向來理解,惡魔可能代表一種具有威脅性的,或者是感染擴散能力的大寫他者。
至於第二個層次的神話學詮釋,薩克引用了一段新約的橋段,就是基督走在路上,有人生病或抓狂在地上打滾,接著基督便過去。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爭議:基督到底做了甚麼事?從我們的角度說,他是在驅魔;但那可能是褻瀆了基督,他不認為他是在驅魔,而是在進行一種神蹟的療癒(miracle healing)。基督走過去問其中一人,「你是誰?」中邪的人回答:「我是軍團」(I am legion)。 後來復活電影常引用這個典故。對薩克而言,以神話的方式來詮釋魔,基本上就挑戰了一與多,或者所謂的創造者跟他創造出來的生命之間的關聯或是秩序,也等於是挑戰了神學治理的秩序。
同樣的,以上兩種詮釋都不是薩克要談的重點。他比較想推的是第三種,他個人獨特的惡魔學視角。他在這裡創造了一個新詞meontological,它是由兩個字組合起來的me+ontological,這表示薩克會從比較本體論的角度來理解魔是甚麼,而這個本體的狀態跟剛剛我們所提到的宇宙的悲觀論類似,大致上都指涉到一個超級虛無的、漠視人類存在價值的世界。
在此脈絡之下薩克開始討論但丁。傳統的解釋都將但丁《神曲》〈地獄篇〉(Inferno)的每一個地景對應到某一種懲罰。每種懲罰代表人在陽世犯了甚麼罪。黃教授提到,這裡的討論令他想到台南麻豆代天府有一個天堂跟地獄的圖像,十八層地獄裡有各種苦刑,每一種苦行對應了罪人在陽間所犯的惡行。這也是理解但丁的典型方式。
然而,薩克不從這個角度來看但丁。他強調的是地景或氣候:地景是由被打入地獄者的肉身所構成的,也就是來自魔化的肉體。對薩克而言,但丁的作品裡如果有魔這個概念的話,基本上都已經跟整個自然景觀融合為一,沒辦法分得很清楚了。所以薩克特別提到附魔(demonic possession),想要提出比較不一樣的解釋。我們一般會認為所謂附魔是一個有生命的人被惡魔佔據了整個生理,但是薩克告訴我們所謂附魔也可以發生在地方、地景上,這其實是有爭議的一個詮釋角度。
第二章一開始提到在西方形上學主流哲學傳統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東西被埋藏在地底下。例如阿格里帕(Agrippa)的《神秘的哲學》(De Occulta Philosophia)。葉慈(Yates)研究這本著作,發現裡面有基督教的與非基督教的傳統,有從埃及來的魔法學理論,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文學,當然主要是煉金術跟神祕主義,或者是夾雜一些古希臘時代的自然哲學。其「神祕」指的是這個世界以能夠被我們察知與理解的方式出現在我們面前,但是這個世界後面那個層次才是神祕哲學或魔法世界的領域;那些我們看不到的、察覺不到的隱藏的特質都是魔法學研究的的領域,例如占卜。
第二章接下來有六個講題,薩克將其分成兩組,第1到3講為第一組,第4到6講則為第二組。第一組涉及魔法陣(magic circle)這個關鍵概念,有點類似舉行宗教儀式的空間,此空間好像可以按照它獨特的規則運作,而且它會被賦予一些禁忌,變成一個禁地。魔法陣透過儀式與咒語等,達到通靈的目標,等於要媒介自然與超自然。
黃教授討論的重點放在六個講題的第二組 (4-6講),談的是魔法陣已經沒有辦法運作,或者失去運作效力的情況。如果魔法陣讓我們進入日常世界看不到的世界的話,這裡的隱藏世界其實已經不需要或不可能有任何的中介了,但它還是以一種很奇怪的方式存在。例如拉夫克拉特的短篇故事描寫奇怪的生物或機器,在形象化後長得像水母或章魚,召喚出宇宙恐怖(cosmic horror),讓自然與超自然間失去任何媒介。當所有界線消失,非人會出現在此時此地,造成知識與語言的崩解。
伊藤潤二的漩渦
在此脈絡下,薩克談到伊藤潤二的故事《漩渦》(Spiral)。故事的開始有一位有怪癖的齊藤先生,他一看到漩渦狀的東西都會對其著迷,停留駐足很久。伊藤潤二的小說有很多有怪癖的角色,例如對頭髮、毛髮與人臉氣球之類的東西著迷,剛開始只是一個主觀的執念或耽溺,到最後卻會變成幾乎無所不在。
漩渦剛開始也是一個概念,一個抽象的象徵,可是後來這個象徵越來越失去控制,有一點類似但丁〈地獄篇〉中人與地景融合為一的狀態。等於是說所謂「宇宙恐怖」降臨到這個世界,讓你完全無法去思考它,更別說要去介入。薩克最後用漩渦的意象帶領我們理解所謂的「沒有我們的世界」,其中人類的行動介入已經是可有可無,不可能產生任何作用。大家也許可以去思考一下,這個沒有我們的世界是否一定是一個外太空世界,也許它不是一個great outside,因為內與外已經無法區隔。
何謂生命?
第三章要講的是生命這個概念。薩克不是從人類的角度去理解生命,他談的是一種滿奇特的生命觀。我們也許會覺得死亡是對生命的否定,但是對薩克而言,其實某個形式的生命結束之後,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形式的生命會延續下去,所以他在書裡面談到亞里斯多德如何區分所謂的存活的生命(the living)與抽象的、大寫的Life。薩克也從這裡帶回恐怖的主題,讓我們了解到其實真正的恐怖,與其說是害怕死亡倒不如說是害怕生命。這種生命是苟延殘喘的、沒有完全結束的另外一種生命形式。
第三章的第4講特別談到跟屍體(nekros)有關的概念。薩克先引用了奧德賽裡面的一個橋段,說明屍體主要有兩層意義:物與life after life。首先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某個生命結束之後留下的東西,它可以稱為死人,或者說這時候屍體已經成為一個物。另一層次的life after life比較複雜,例如地獄裡的存在並不能從第一個層次的物的角度來理解。那麼如果說屍體可以被理解成life after life的話,很顯然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生跟死之間沒有一個對立的邏輯,沒有這麼清楚的切割的關係。
接下來延伸出來的一個問題是,某種形式的生命結束之後,什麼東西繼續存活下來的問題。這是一個複雜無比的神學問題,會涉及耶穌基督開啟的,很難概念化的「復活」的問題。薩克接下來就提出一個神祕屍體 (mystical corpse) 的概念:當一個生命結束之後,它可能必須以某個形式延續下去,這就是所謂復活。在「國王的兩個身體」的討論中,當大家高喊「國王死了,國王萬歲!」時,我們看到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國王的肉身結束之後,如何能夠讓國王所代表的統治權的正當性能夠繼續延續下去,所以就必須要提出另外一套所謂的神祕的身體。後來這個問題所牽涉到的不只是個人層次,已經變成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或是政體的最核心的概念。人類歷史的演變決定於我們如何處理屍體。
黃教授指出,談生態的人常會談到薩克這本書,有人會認為假想人類消失,留下沒有我們的世界,根據的還是人類不存在的想像視角,仍是人類的自戀想像。但梅雅蘇談到,估算約4億六千年前存在的隕石有其相當程度的絕對性,它的世界是沒有人的世界。此處講了很多類似像《明天過後》的情景,他認為這些仍是人類恐懼焦慮的投射。他請觀眾反思這類文學詮釋上的問題,究竟這些電影真是處理沒有人的世界的問題,還是只是典型人類想像或恐懼焦慮的投射。
Q&A
討論一:生命的定位
接下來進入Q&A時段,主持人兼與談人李育霖教授首先提出他的看法與問題。他認為薩克提出的哲學的恐怖比較不是從人的角度去看,而是具體化了一個叫做哲學的恐怖的東西。他的感覺是:好像這個世界被挖出了一個巨大的黑洞,黑洞裡甚麼東西都沒有。薩克用空無(void)這個字來描述這個黑洞。李教授首先提出的問題是人們如何去思辨、想像或感知這個巨大的空洞。薩克一直在講這是一個沒有我們的世界,它不只是「世界自身」,而是在我們內部一個巨大的空洞,是我們的思想沒有辦法抵達、想像、命名與思考之處。
薩克提出空無的概念,是屬於超驗的(transcendental)的立場,那麼在哲學的恐怖的脈絡下,生命(life)是超驗的的嗎?李教授比較德勒茲的生命概念與薩克在另一本書After Life裡面提出的生命概念,發現有許多可以互相對話之處。對德勒茲來說,生命是純粹內在(pure immanence)。例如狄更斯小說中有一個行為乖張的流浪漢,被眾人厭惡詛咒,突然有一天他快死了,大家卻開始努力關心他,使他又活過來了。德勒茲的讀法是:也許流浪漢平時是不名譽之人,然而在生與死之間有某個時刻,讓真正的singular life出現,這樣的狀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今天所談到的不可名或不可知之無物。
所以大寫的Life是超驗的嗎?它又與life 有何關係?我們能否進一步談after life是什麼樣的life,或者我們剛剛講的生命 (life) 和活物(the living)間到底有什麼關係?薩克是如何理解大寫的Life 與一般我們所談到的活物(the living)?而恐怖又是如何介入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的主題是媒介 (mediation),那麼薩克提出一個有趣的對媒介的理解,談的是媒介無法觸及的境域,但這個境域還是得透過媒介去理解,因為他說要了解世界,仍要從無(nothingness)去了解,仍要從另一個世界去理解,他如何去解決這種思維的二律悖反(paradox)?透過哲學的恐怖,薩克究竟想做什麼?李教授也提到哲學的恐怖與德勒茲的「流變成惡魔」(becoming-monster)可以做比較。
黃教授回應道,亞里斯多德區分活物與大寫生命是一個簡單的區分。所謂的活的(living)是指會動的、會變的與會吃的東西,是常人認知的活著這件事;而另一個比較複雜的層次是亞里斯多德所談的生命的法則,是所謂大寫的靈魂。簡單來講可能就是人的生命有各個不同的階段,它會慢慢的讓生命的原則能夠彰顯出來。以白馬非馬的例子來說,馬的本質或者馬的生命法則會經由幼馬到成年馬的實質轉變(morphology)的過程,去實現其抽象的生命法則。
黃教授提出薩克好像在惡搞亞里斯多德,他會特別強調所謂的大寫的、抽象的生命法則跟活物(the living)之間的斷裂。他舉出很多要死不死的生命,特別是恐怖文學裡,像喪屍、吸血鬼或惡魔這些族群。他們看似像living,但是已經沒有生命的法則。
黃教授接著從這個角度回應李教授對於薩克想做什麼的疑問。他認為至少薩克找出一條新的路徑,以及如何跨領域之類的新思考,也找到新的研究對象。他讓我們知道,原來嚴肅的學術研究也可以談比較流行的東西,例如魔法學、諾斯替等議題。所以他帶給我們一種新的做哲學的方法,也有點像後設思考,其實也在思考哲學的邊界在哪裡,不止是停留在西方形上學的啟蒙,或康德等等的框架中,而是要把做哲學的方法推向一個新的方向。這並不一定要找到新的東西,像拉夫克拉特、叔本華或但丁的《神曲》,已經很多人講過。一般正統哲學史都認為叔本華是存在主義的先鋒,那如果是在存在主義的架構裡面,就還是在人的脈絡裡面,所以會思考苦難,悲劇,哲學等等。但是薩克都不從這些角度來談叔本華,所以也許不是惡搞,而是重新再去詮釋西方的哲學。他所謂的哲學恐怖其實也是一些基本概念的重新定義,例如無(nothingness)、否定(negation)、單義生物(univocal creature)、有機與無機(organic and inorganic)和界限(limit)等概念。其實人無時無刻都處在單義的的狀態,在我們的生命裡保留許多演化過程的痕跡,我們身體裡有很多化石,不只是有機的的存在而已。比如說人死的時候,身體的各部分要結束都需要時間,可能最早終止運作的是大腦,可是大腦終止運作之後,人的植物性機能(vegetative function)要一段時間後才結束。所以有時候會有陰屍,某個形式的生命,例如微生物、菌類等,都還在屍體上繼續成長,也等於是某種沒有人類的世界,是另外一個形式的生命,它本質上是單義的。另外,黃教授覺得做哲學的人都要有這種能力,我們平常常講的詭奇(uncanny),到底我們真的很確定我們在講的是甚麼意思嗎?所謂的界線、否定、超驗的(transcendental)與內在的(immanent)這些單一的字詞,不應該把它們視為理所當然。
討論二:太過寫實的恐怖文類
提問人二提出,現在非常流行日本的恐怖殺人漫畫,要如何去分析日本人在描述變態或殺人的這種太過寫實的虛構?
黃教授回應道,如果日本作品太過寫實而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對恐怖的理解時,背後的思考其實涉及日本恐怖片與我們所習慣的整個西方好萊塢式恐怖片不同。例如西方的graphic horror就是強調把人的身體支解。像伊藤潤二這類作品,你會覺得它不是只有一個層次而已,而是還有一些美學化的色彩,使恐怖變成是一種美學想像或形式上的經營。不過也許最後的問題就是,也許我們不要期待讀了薩克後,就可以有一套可以拿來分析這個或那個恐怖形式的理論框架。如果是這樣,等於沒有真的進入他的世界;他所談的恐怖是比較本體性的,而非工具性的。
討論三:理論的適用範圍
提問人三高珮文指出她目前正在研究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小說,裡面也有惡魔與大自然場景的描寫以及印地安附魔之說。她提問是否能將薩克這一套論述工具化的套用到南方研究,例如南方哥德小說(the gothic novel)。
黃教授認為我們無法直接將薩克這一套論述工具化地套用到南方研究,但若要做其實也是可以。我們可以想像一下,除了威脅主體的大他者或者人類焦慮的恐懼投射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研究恐怖類型文學的可能性。所以薩克的論述還是可以用,但是用的時候必須要知道恐怖文學的研究跟傳統的文學研究差別在哪裡。另外,薩克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就是他回到了一個比較偏向哲學本體的層次。文學批評常把論述工具化,可能就不會去追問背後比較複雜的思想脈絡,比如說所謂西方哲學除了理性之外還有什麼,或者基督教信仰成為正統的,知識或宗教體系的秩序,是經歷了甚麼樣的鬥爭過程,把甚麼東西排除在外,如何把那些東西再挖回來等等。所以除了工具化的使用,我們也可以更積極一點,去探究論述背後所牽涉到的,比較複雜的層次。
討論四:誤讀與媒介
提問人四金儒農提出,這本書最令人感到困惑跟無法進入的原因是,他好像很難跨越純粹理性思考,但這本書甚至認為我們要進入一個unthinkable world。但他覺得有趣的地方是他後來有超前看了「哲學的恐怖」三部曲中的第二本,其中薩克把笛卡爾的哲學論文當作恐怖小說在讀。笛卡爾必須要先構想出一個惡魔,他可以遮蔽我們所有的感官,讓我們以為我們存在,他特別強調笛卡爾構想這件事情後就逃開了,他不能去碰觸那個問題,因為對他來講那是一個哲學無法到達之地。第一次讀書會選擇薩克這本書容易讓人產生一種誤讀,他老是在想這本書跟媒介的關係是甚麼,他認為對於這無法思考的世界,我們唯一的選擇會不會其實是透過這些不能思考的東西或是魔做為媒介,去碰觸其他我們不知道在哪裡的東西。所以我們最後還是要回歸到實做的問題,也就是操作上我們需要注意什麼?
黃教授認為這個問題用比較學術的,或者是哲學論證的角度來回答的話,也是在思考我們如何去思考人類心智活動以外的世界。這是一 個當代理論的大問題,之前的新唯物論研讀會也許跟這個問題也有點關係。在所謂的現象(ontic)背後,在客觀科學實證的層次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談物的可能性,有沒有一個不會對我們彰顯的本體的(ontological)層次?當代哲學論述中,有人會從非人轉向(nonhuman turn),或是新媒體、新唯物論與思辨實在論的方向來談這個問題。薩克在這樣的哲學脈絡裡面佔有一個獨特的位置。他想用人類心智不能及的某種現實,去回應當代的各種理論轉向。
討論五:伊藤潤二與哲學的恐怖
提問人五指出伊藤潤二與哲學的恐怖相呼應之處或許在於他不會解釋恐怖的根源。像漩渦的故事,各種恐怖與荒謬都指向漩渦,好像有一個巨大的力量在支配一切,但你無法抵抗。
黃教授談到幾年前曾幫比較文學學會的會訊寫過有關富江的文章。那一期編者最後要他加一句話:「我們都是富江!」這是耳熟能詳的當代理論套路,我們都是賽博格,我們都是牲人之類。可是這會不會言過其實?如果參考伊藤的訪談,我們會覺得他好像又沒有薩克所講的那麼激進。他的富江系列只是要談人的問題:人的過度沉迷。他想諷刺與批判日本文化那種追求完美到極盡瘋狂的狀態。這些狀態濃縮到富江身上,所以講到最後可能我們都是富江,我們從富江裡面看到自己的形象。可是問題就在:難道這些作品只能按作者提示來讀嗎?所以某個層面上你會覺得薩克講得太多,可是某種程度上的支解或扭曲,有時候是必要的。透過較激進的角度去從事文學詮釋或者哲學思考,我們才容易跳脫一般對於伊藤作品的詮釋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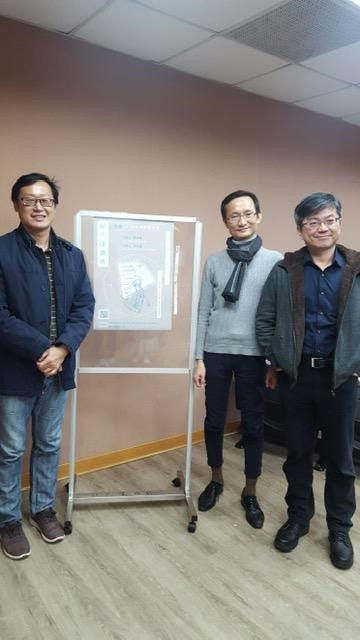
(主持人李育霖老師、主講人黃涵榆老師及研讀班主辦人邱彥彬老師於會後合影留念)
